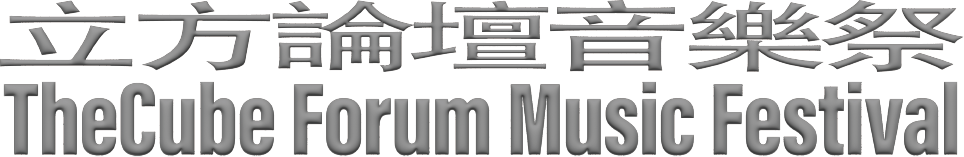The following featured Chinese articl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典藏ARTouch.
作者:沈柏逸
12月台北,黑暗的烏雲中縈繞著殘酷衝擊與撫慰治癒,不可見的空氣仍然瀰漫病毒、焦慮、壓迫、戰爭與恐懼,台北的呼吸頻率感染著「聲波薩滿」的毒與藥,音樂祭餘音殘響不絕地散播各個角落,封閉治理的未來陰霾在黑暗聲波的衝擊中透露一絲開放契機。在此,我們必須回應身體接受的高張聲響、必須創造異質的器官、必須繞經深不a見底的黑暗而改變無望的未來。
12月台北,黑暗烏雲籠罩台北天空,陰雨濕冷地滲入皮膚內裡。我們自我囚禁在室內空調、和緩音樂、迷因貓咪與串流平台藉演算法推送的個人化節目。城市與行動載具的視聽媒介不斷調控我們的感知,演算法的數據巨獸不斷同步我們的數位軌跡,從城市到行星的整體規模迴盪著單一的技術節奏(註1)。曾經把人們聚合的集體記憶不在,看似連結大家的演算法加劇了隔絕、孤立與分裂的情境。疫情、戰爭、鎮壓的焦慮與恐懼影響我們,濃稠的黑暗憂鬱滲入骨髓,也曝露到外在氣象。過完12月,明年還是必須服從單一節奏的徹底絕望。

聲波薩滿」Seething Mass演出,2022.12.10。場地:恆成紙業,©立方計劃空間,攝影師:林政億
體驗的治理或解放?
同樣12月台北,線性時間瞬間停滯,「聲波薩滿:立方論壇音樂祭」(聲波薩滿)音樂祭變造的樂器與音響系統作為「器官」不斷增幅聲波,低音震動的頻率也撼動我們的五臟六腑、DJ猶如切開內臟再縫合不同文化與時空的文本跟樂種,「感官體驗」的調度更是讓我們感覺到感知的複雜性,不再只耽溺於視覺奇觀(Spectacle)(註2)。
然而,過度強調「體驗」,不也跟全台各大藝術節一樣,淪為放煙火吸引人潮觀光的狂歡嘉年華,成為城市精緻治理的體驗式經濟?或者像是城市的夜店,用四四拍(通常是techno),讓人在工作壓力之餘,找到出神放鬆的時刻,成為殭屍的搖擺抖動?難道只是想復古懷舊1990年代後工業藝術祭的DIY式龐克暴亂?
對照於當今我們慣習的「體驗式經濟」的魔幻治理,「聲波薩滿」透過許多「演說式表演」(lecture performance)的語言文本解構純粹直接的聲音體驗,召集許多視覺藝術家參中演出。儘管如此,大多演說式表演都限於「演講」的再現創作或研究脈絡,缺乏「表演性」的複雜轉化。但演說式表演豐富的後設展現,可以從張紋瑄跟區秀詒在牯嶺街小劇場的表演窺知一二。

「聲波薩滿」張紋瑄演出,2022.12.11。場地:牯嶺街小劇場,©立方計劃空間,攝影師:陳佩芸
張紋瑄透過解構政治人物用「姿態」控制人的潛意識,聰明地分析與拆解動作,除魅政治人物如何操弄情感與國族神話,卻較少藝術複魅著魔的暈眩感。況且在「聲波薩滿」的音樂祭脈絡,不也可以後設除魅一下表演者表演到忘情投入擺頭的姿態?表演者的身體姿態不也是一種對觀眾的政治操控嗎?
相反的,區秀詒則是復魅地用魔術幻燈投影(Phantasmagoria)(註3),讓鬼魂的聲音(藉由老式隨身收音機四散在觀眾席)與影像飄蕩在黑暗的環境四周(歪斜投影),表演的不是表演者的身體姿態,而是投影光束與剪下的影像遊魂。聲音與影像立體地與觀眾「同在」(而非在銀幕上再現),她也最現地製作(site-specific)地跟空間脈絡對話,幽默虛構「牯嶺街被捅殺的鬼」的餘生。除了演說式表演的除魅與復魅,聲響表演則更加打碎和諧的主旋律假象,呈現失調衝擊。

「聲波薩滿」區秀詒演出,2022.12.11,場地:牯嶺街小劇場,©立方計劃空間,攝影師:陳佩芸
失調:危險脈衝的振幅
假如夜店音樂通常再現適度的危險感,讓人可以在工作壓力之餘放鬆,那在「聲波薩滿」則是放大鬼魂暴戾跟動物野性成危險衝擊,直接打到觀眾內在,有如臟器發病,既痛苦又愉悅地矛盾翻攪。在The Wall表演的新加坡天文台樂團(The Observatory),以百鬼夜行的廟會姿態,鼓聲低音震撼低鳴開場,實驗性跳接在不同類型的音樂中,幽微地結合政治反抗的力量。不同於在歌詞中直接對政府極權的批判,他們以異質性的複雜歌曲操作,配合樂器不同的轉化與改造,打開音樂的政治性維度。後半段惡魔變音地重複唸出「imprisoned mind」(被囚禁的心靈)與「dreams revolution」(夢想革命),更是讓音樂表演提升到政治轉型的批判空間。不淪為政治藝術的單一話語說教,而是在過度危險的聲響中飽含迷幻漩渦的不安與抵抗力量。

「聲波薩滿」天文台樂團演出,2022.12.08,場地:The Wall Live House 這牆音樂展演空間,©立方計劃空間,攝影師:林軒朗
對於話語的解構與重新操作,埃及藝術家哈桑・汗 (Hassan Khan),有如巨熊壓頂般地用低音暴力壓得大家窒息(技術哲學家許煜在第一排搖擺的遞迴反饋演算法音樂放大的力量)。他自行作曲寫詞,用演算法解構自己預錄好的嘻哈樂句,現場調度並搭配電腦隨機演算與無限的取樣搭配重組。相較於展覽「液態之愛」完全由程式隨機演算的聲音組成,現場演出的人為介入更暴力地放大嘻哈節拍,狂震得耳朵與腸胃不要不要;相較於夜店嘻哈音樂的適度危險,哈桑讓人感到演算法無限的崇高與恐懼(註4)。

「聲波薩滿」哈桑・汗演出,2022.12.08,場地:The Wall Live House 這牆音樂展演空間,©立方計劃空間,攝影師:林軒朗
爆裂窒息的轟炸後,日本的DJ Sniff則是以滑溜的八爪章魚姿態出場,極簡又物質性地操作數位唱盤與刷碟噪音,瘋狂手速與唱盤融合成一具名副其實的賽博格「怪物」。他不只是再現音樂,而是凸顯「聲音的物質媒介」。經歷哈桑像巨熊壓頂的厚重窒息,DJ Sniff則是輕巧與彈性地悠遊在液態之海裡,中後段的高音波更讓人感到內省與抽象的模糊感受。

「聲波薩滿」,DJ sniff演出,2022.12.08。場地:The Wall Live House 這牆音樂展演空間,©立方計劃空間,攝影師:林軒朗
屍調:非人的極限體驗
讓我們快轉到工業感的「恆成紙業」,紙廠空間布置上刻意的螢光塗鴉儘管讓我感到意興闌珊,但現場堆疊的紙樣、電風扇上的厚重灰塵,以及建築使用的鬼魅痕跡卻更加勾起我的注意。
徐嘉駿在陰雨下午震撼開場的無輸入(no-input)工業冷硬感,如末世火山爆發的低鳴,震到紙廠紙樣跟地板都劇烈晃動,電扇上灰塵相信掉落不少,腳底下的塵埃屍骸也隨聲響湧動,從腳底按摩到身體內部。不見當代DJ潮流的花式剪接,在毫無燈光特效的黑暗暴風中,耳朵被純粹的反饋聲響逼到無路可退的邊緣,整個紙廠跟細塵都在晃的唯物性在極限邊緣開顯。有如媒介哲學家尤金薩克(EugeneThacker)繼承叔本華的宇宙悲觀主義,用深淵、宇宙黑暗、非聲響(unsound)的方式,談「徹底否定」一切人類語言與聲音意義的窒息高壓與絕對暴力。

「聲波薩滿」徐嘉駿演出,2022.12.10,場地:恆成紙業,©立方計劃空間,攝影師:林政億
在菲律賓聲響藝術的造聲互動歷史再現及演講後,菲律賓團體Seething Mass的表演則刷新觀眾耳目,徹底逃逸聲響學術歸類的框架,不只聲音讓人振奮、視覺也充滿創造性。表演場合的VJ通常是螢幕保護程式的生成式3D建模或抽象流動的濾鏡,讓人覺得視覺調味麻痺。然而,Seething Mass的影像充滿著實驗電影的內斂質感,拆遷紀錄、科學影像、達達主義式的疊圖與拼接,在具象的影像中縫合異質屍塊,在聲響上更是表現深淵地獄的混雜模糊感,進而拆解與重構人類和諧的秩序。
林強帶著一尊小佛像轉化多層曲風,聲音內斂地融合環境、佛學與山水氛圍,帶給人更加內省的感受。相較來說,最後鄭道元的DJ如壓軸反轉地炸裂全場,堪稱「聲波薩滿」最出神、暴動、狂烈、抽蓄、同時讓觀眾比殭屍更殭屍的現場演出──如果說夜店讓聽眾如殭屍抖動放鬆,那鄭道元則是讓聽眾變瘋狂喪屍。整個場域跟觀眾的身體像無政府主義般爆裂地融成一團漿糊,想抵抗規訓的身體不由自主地被法西斯般的舞曲控制。鄭道元暴力跳接與融合暗黑氛圍、神聖吟唱、暴力槍響、影集《雙峰》主題曲、閃現烏克蘭國旗影像,同巧妙地調度大眾文化的集體記憶,如濱崎步的電音舞曲以及最後《當愛已成往事》的「只要有愛就有痛」,神聖粗俗並置,更是讓整個紙廠煽動著附魔的躁動(註6)。

「聲波薩滿」林強演出,2022.12.10,場地:恆成紙業,©立方計劃空間,攝影師:林政億

「聲波薩滿」鄭道元演出,2022.12.10,場地:恆成紙業,©立方計劃空間,攝影師:林政億
詩調:黑暗的集體轉型
最後一天牯嶺街小劇場雷光夏的表演,讓我產生了意識想抵抗但身體卻還是起了反應的矛盾情緒。在受過當代藝術、前衛聲響、工業音樂的洗禮後;雷光夏空靈嗓音與詩意歌詞,再加上鍵盤及弦樂撥奏的古典審美,即使配合DJ誠意重的干擾也沒法抵擋和諧溫暖的旋律聲線,觀眾彷如在後現代資料庫的全面碎片化後(註7) ,重返人性大敘事。儘管如此,我還是在終曲《黑暗之光》下不由自主泛淚,追憶隨時間改變的自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小明絕望地說「這個世界是不會為你而改變的」;雷光夏的詞則是在遭遇巨大黑暗能量後自我轉型的「黑暗溫柔,改變過我」。

「聲波薩滿」雷光夏演出,2022.12.11,場地:牯嶺街小劇場,©立方計劃空間,攝影師:陳佩芸
過於龐大的黑暗漩渦既可以高壓暴力地讓人坐立難安,也可以撫慰受創精神,無論如何「聲波薩滿」的「黑暗氣旋」都在我們身體深層「起了作用」,我們也必須用身體回應這些表演者發出的聲響;我們不再只是旁觀拍照打卡或服從治理的觀眾,而是同時用聽覺、身體、皮膚毛孔、器官與記憶全面參與地共同演奏。我們能夠像DJ靈活挪用與重組治理生命的單一節奏,把強烈的感受能量推到邊緣,暫停目的論的線性時間,終止演算法與新自由主義不斷欲求的功績主體與光明現實主旋律。極致地以擾亂感官的迷幻與間離美學,創造絕對真實的虛構場(註8) ,與動物、鬼魂、灰塵、死亡、脆弱與黑暗的幻肢集體,共同「失/屍/詩調共鳴」。

「立方論壇音樂祭─聲波薩滿」豬腳跳舞空間設計,2022.12.11,場地:牯嶺街小劇場,©立方計劃空間,攝影師:陳佩芸
12月台北,黑暗的烏雲中縈繞著殘酷衝擊與撫慰治癒,不可見的空氣仍然瀰漫病毒、焦慮、壓迫、戰爭與恐懼,台北的呼吸頻率感染著「聲波薩滿」的毒與藥,音樂祭餘音殘響不絕地散播各個角落,封閉治理的未來陰霾在黑暗聲波的衝擊中透露一絲開放契機。在此,我們必須回應身體接受的高張聲響、必須創造異質的器官、必須繞經深不見底的黑暗而改變無望的未來。
註釋
註1 關於城市的單一運算與多重節奏辯證,可以參考哲學家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提出對城市治理的單一節奏跟身體內在多重節奏的交互影響。他指出「要想發生變化,一個社會團體、一個階級或一個社會等級必須通過在某一時代留下節奏的印記來進行干預,無論是訴諸武力還是通過諂媚。」(Lefebvre, H., translated by Elden, S. & Moore, G. “Rhythmanalysis: Space, Time and Everyday Life.”New York: Continuum Studies In Philosophy. 1992.)
註2 高森信男梳理過視覺藝術中非視覺的體驗,然而卻沒注意到這樣的五感體驗早被單一節奏的「體驗式經濟」收編。我在「學實學校」講座與文章中也不斷提到體驗早已成為另一種「新的治理術」。
註3 關於魔術幻燈如何制幻,可以參考Noam M. Elcott精彩的媒介考古文章《魔術幻燈部署:身體與影像的真實時空集合》。
註4 許煜的《遞歸與偶然》也處理從哲學家康德到里歐塔的崇高美學。他更進一步把崇高作為現代技術治理的出口。(許煜著,蘇子瀅譯,《遞歸與偶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
註5 尤金薩克提到非聲響的徹底否定「非聲響的東西——就像一棟建築,或者一個心靈——總是不穩定的,不斷地要崩塌。但非聲響也不同於聲音和沈默的對立(一種反聲音),就像它不同於所有聲音現象的相對性(超-音或次-音)。一個非聲響的聲音也許類似於否定神學神秘主義傳統中的『不知』一詞,其中『不』的前綴是一種撤消或解開,既表示對知識根基的否定,也表示對一個絕對極限的悖論的理解(apprehension)。」(Eugene Thacker, “Melancology:Black Metal Theory and Ecology,”Zero Books, 2014)
註6 鄭道元不像The Wall場後段的可預期曲風,讓人順暢擺動,而是異質暴力與不協調的拼接。
註7 大敘事終結後的「資料庫拼貼組合」問題,可以參考日本哲學家東浩紀的《動物化的後現代:御宅族如何影響日本社會》或者媒介理論家馬列維奇(Lev Manovich)的《新媒體的語言》。他們都不約而同呼應如今不再有完整大敘事,而是碎片化的資料重組與不斷拼接,在我看來恰恰能跟今天碎片化的串流與DJ文化呼應。
註8 藝術理論家Jean-François Chevrier在文章《藝術幻覺:在恐懼和狂喜之間》,提到「必須長時間、廣泛地、有意識地打亂各種感官,詩人才能成為通靈者。」此外,他也提到「幻覺,既可以是視覺的,也可以是聽覺的和觸覺的,它相當於是一個載體,如果借用佛教的用語那就是『乘』,承載著另一個完全不同的現實,以間離的、非現世的形態取代了事物真實的存在。同理,亞陶反對將『存在的假象』(lie of being)等同於『幻覺的真相』(truth of hallucination)。」換言之,相較於日常的經驗現實,藝術創造幻覺的真相更為「真實」。(Jean-François Chevrier, “Between terror and ecstasy Artistic hallucination,”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