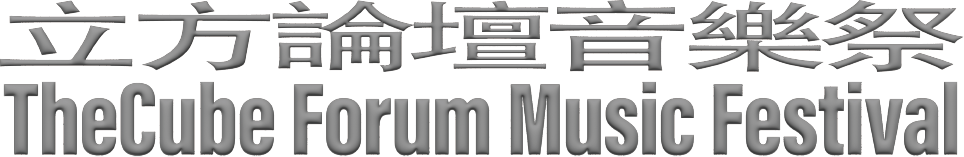文章來源:數位荒原
作者:夏菉泓 / 編輯: Rikey
2022年末,在遍布全台的音樂祭中,「聲波薩滿-立方論壇音樂祭」以奇特的存在姿態,在無論獨立音樂、電子音樂、噪音實驗或當代藝術領域中,皆引發了嘈雜且多元的討論聲。為期四天的「聲波薩滿-立方論壇音樂祭」,在四種場域發聲,其中包含音樂、聲音、表演、論壇,演出者或在獨立音樂演出空間中,就著重低音金字塔音響震響聽眾臟腑,亦有在恆成紙業倉庫中的紙樣棧板間,與工業扇及塵埃間發聲,不同的表演性質,以各異的方式與聽者 / 觀者的身心腦發生連結。

TheCube Forum Music Festival—SONIC SHAMAN, 2022.12.08, The Wall Live House, ©TheCube Project Space, photo by Hsuan Lang Lin
本系列專文分別針對性質不同的表演者,紀錄、爬梳及回顧,包含梳理新加坡資深獨立樂團天文台(The Observatory)與政府治理的歷史關聯,菲律賓聲響文化學者達鴦・雅洛拉(Dayang Yraola)的現場聲音工作坊及講座,並邀請臺灣書寫作者回顧從獨立聲響到當代藝術場域演出的歷程。透過不同的位置與發音方式,回應外在環境自城市空間、文化治理,乃至於聲音對聽者的特有的情緒、記憶與身體解構、重塑或穿透力。2023年初,世界依然紛擾卻表面同質,我們如何擁有一種新的基礎,重新寄盼自身與過往及未來發生關聯的方式?這些不同文化背景的演出者,也許揭露了一些來自歷史的聲音訊息⋯
像早晨一樣自由
像夜晚一樣自由
但你在這裡永遠不自由
而我在這裡永遠不自由
—天文台樂隊,〈廢壞人生〉(Waste Your Life)
Waste Your Life by The Observatory on Youtube
噤聲,是天文台的一個起點…
1987年5月21日,新加坡政府發起了一場大追捕行動—光譜行動(Operation Spectrum),在無預警的情況下,根據《內部安全法令》(ISA)逮捕了22個人,其中包括長期致力改善移工境遇並敢於直言批評政府政策的天主教社工文森特・鄭,以及經常為移工發聲同時也是工人黨支持者的律師張素蘭。新加坡政府宣稱這些人意圖以「馬克思主義陰謀破壞新加坡既存社會和政治制度,使用共產主義統一戰線策略,目的是建立一個馬克思主義國家」(註1),即使手中並不握有實質證據。1989年6月,新加坡政府頒布了附屬立法,要求五人以上集會必須先取得警方許可。2006年9月,新加坡主辦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年會,引來許多國際非政府組織和公民團體前來進行示威活動,抗議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新自由主義政策。2007年,新加坡反對黨結合一小批緬甸國民至東協峰會示威。2009年,新加坡政府宣布將要審查《公共秩序法》,並於4月通過,公共領域再次向內限縮。(Rajah,2021)
新加坡法律學者喬西・拉賈認為:「《公共秩序法》可以理解為是一種立法,它增加了政府對『國家』公共空間進行意識型態同質化的程度。」(Rajah,2021)新加坡政府對公共領域的限縮壓制已有很長一段歷史,這遠到可以追溯回1966年的《破壞公物懲處法令》。這項法案是由新加坡的國防部長提出,旨在打擊反對派於公共領域宣示支持越共、反美的示威行為。冷戰期間,親西方的人民行動黨不斷邊緣化、妖魔化「共產主義」,試圖將左翼勢力趕出新加坡的政治領域。當時由人民行動黨之派系分裂出去組織而成的社會組織陣線是對抗人民行動黨的主要勢力,他們反對殖民主義,主張社會主義,抵制國會與施行壓制性法律的國家機關。拉賈認為《破壞公物懲處法令》是新加坡政府對於社陣所領導之反對美軍介入越戰行動的回應。這項法案中的破壞行為指的是—根據李光耀總理的描述—「一種特別惡毒的社會輕微罪行,例如拿一罐油漆到每個公共巴士站,或是用粉筆寫出反美、反英或親越共的口號。」(Rajah, 2021)法律條文的建構作為國家機關意志的展演,在這套公開的腳本中,毀損者被轉化為「犯罪者」而非「政治行動者」,「宵小」而非「烈士」。

TheCube Forum Music Festival—SONIC SHAMAN, The Observatory Performance, 2022.12.08, The Wall Live House, ©TheCube Project Space, photo by Hsuan Lang Lin
1974年,新加坡政府通過了《新聞紙與印刷品出版法》,出版法賦予了國家權力,使其能監視和管理報紙的所有權、經營管理與資金狀況,新加坡在1986年再度提出針對「外國媒體」的修正案。出版法規定所有報紙都必須具有兩級股份結構:管理股與普通股,而管理股在人事任免方面具有大過普通股好幾倍的權限,且只能由國家機關核可的個人和公司持有。這項法案施行之後,所有的報業公司皆是由政府代理人或是政府所指派的人負責經營,不符合國家意識形態的人或思想將無法受容於組織之中。而「人民」在這整套法律論述中被弱化為智力有限、欠缺批判性思考能力、處理不了複雜事物也無法自己評估事態的存在。「人民」被當作幼童對待,國家機關的權力獲得提升。這是天文台樂隊的其中一個起點—被高度同質化的公共空間,被噤聲的公領域,被馴化的公民社會。
小眾實驗空間,是天文台的另一個起點…
1960年代是新加坡在地音樂場景的黃金年代,當時西洋音樂的新浪潮席捲新加坡,鼓舞激勵了許多年輕人組織自己的樂團,在地音樂場景開始蓬勃發展。但隨著新加坡在1965年獨立,英軍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撤出新加坡,本土樂隊在營區和英軍俱樂部表演的機會劇減。另一方面,面對嬉皮文化傳入新加坡,長髮和喇叭褲開始蔚為流行,毒品和性解放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對抗性力量,讓新加坡政府在1970年代採取強硬措施試圖「防堵」這股來自西方的「不良影響」,包括禁止男性蓄長髮、增收夜店和音樂展演空間的稅金,禁止西洋搖滾樂團入境演出(如英國搖滾樂隊齊柏林飛船就曾被禁止進入新加坡,日本音樂家喜多郎也曾因此被拒於新加坡國門外。)長髮禁令一直到1980年代才逐漸鬆綁,但新加坡的在地音樂場景在經歷這些變化之後,榮景已經不復以往,沈寂了十幾年之久,許多樂團都黯然解散,音樂人開始轉換跑道或到海外尋找機會,同時,新加坡的反叛文化也受到強烈的抑制。

TheCube Forum Music Festival—SONIC SHAMAN, The Observatory Performance, 2022.12.08, The Wall Live House, ©TheCube Project Space, photo by Hsuan Lang Lin
1980年代新加坡政府對於反叛文化的規制逐漸鬆緩,新加坡的地下音樂場景也開始出現騷動。到了1990年代,一間叫做「電力站」(The Substation)的獨立展演空間的出現,為當時相對缺乏小眾、地下、前衛等元素的新加坡音樂場景帶來了新的活水。電力站是舞台劇導演郭寳崑向政府提議,將一座廢棄的發電廠改造為展演中心,提供較為實驗、小眾的藝術組織演出的機會。電力站的成立迅速推動新加坡藝術圈的發展,而位於電力站一旁的 The Substation Garden成為新加坡地下音樂場景中重要的存在,許多新加坡獨立樂團與實驗樂手都在此地成長茁壯。電力站作為一個中心節點,供原先在國家各式治理之下隱形、銷聲匿跡、不被允許存在的形貌、聲響、實踐在此匯流、碰撞,展演並互相觀看。這也是天文台樂隊的另一個起點:允許一切存在的社群空間。
自我推翻分解,與他者重塑抵抗的噪響
現在我們來談談天文台樂隊本身。在2022年末「聲波薩滿-立方論壇音樂祭」率先登台的天文台樂隊,是來自新加坡的迷幻搖滾實驗樂團。成軍於2001年,期間歷經多次團員更迭,作品風格更是跳躍多變,從前期TIME of REBIRTH、BLANK WALLS、A FAR CRY FROM HERE等作品的電氣迷幻,DARK FOLKE時單用吉他、人聲鋪疊出的抑鬱噪甜,CATACOMBS時的冰冷殘暴無機,GEZEITENTÜMPEL的冷調細緻,OSCILLA的壓抑鬱憤,CONTINUUM結合了甘美朗與非洲傳統節奏、挪威早期電子音樂融匯而出的對稱、重複與恍惚,一直到AUGUST IS THE CRUELLEST,金屬色澤的riff強佔聽者的耳道,不間斷的反饋持續試圖破壞表面上的祥和,「一部高度政治性的噪音作品」(註2),其簡介上如此寫著。在2018到2020年間,他們先後與MoE、Acid Mothers Temple、Haino Keiji合作,探索各種可能與際遇。2019年,主要樂團成員Leslie離團。

TheCube Forum Music Festival—SONIC SHAMAN, The Observatory Performance, 2022.12.08, The Wall Live House, ©TheCube Project Space, photo by Hsuan Lang Lin
2022年,以三人編制發行第15張專輯DEMON STATE。在DEMON STATE中,堆疊了各種臥室錄音、非人聲節拍、日記、過去的取樣,加入了更多即興與噪響。與電子音樂人Koichi Shimizu的協作,天文台樂隊開展出一種更具節奏性、更加電氣化的聲景。這張專輯是「針對無數邪惡和極權主義之起源的深入挖掘:包括全球的惡托邦、於土地上爬行的貧苦之人、猖獗的東南亞資本主義與新殖民主義,以及撒旦」(註3),其精神是在羈繫、隔離與精神性死亡遍佈之際,仍然要「盡一切可能進行抵抗」(註4)。
開放與不確定性,無法歸類的元素與質地,裂變、撞擊之後幻化出驚天異響。除了保持開放,天文台在創作上也不斷進行自我推翻,如同樂團成員袁志偉在過去一次訪談中曾經提到的那般:「(天文台)主要的意識形態只是嘗試,實驗,並允許失敗。如果我們不允許自己這麽做,新的有趣的東西就不會出現。」(註5) 在意識形態與實踐上從來不按主流市場標準行事的他們,不屈服於任何來自聽者或社會的期待。那麼什麼才是天文台所造之音在回應的?天文台的成員王瓔瓔曾說:「我們經常討論或抱怨社會政治問題或發生在我們周圍的不公正的現象,這些想法不可避免地影響或滲透到音樂和素材之中。我們的音樂說起來其實更像是一種自我的表達。」(註6)什麼才是天文台創作的脊柱?「社會政治意識比音樂理論更能指導我們做音樂。它訓練我們忠於自己,不被那些壓迫我們的東西所影響或分散注意力。」(註7)袁志偉在同篇訪談中如此說道。

TheCube Forum Music Festival—SONIC SHAMAN, The Observatory Performance, 2022.12.08, The Wall Live House, ©TheCube Project Space, photo by Hsuan Lang Lin
天文台所演奏的,遠不只是節奏和噪響,或者我們也可以丟棄「演奏」一詞,說他們是在「實踐」一種對歷史、對體制、框架的挑釁—在萬物噤聲之所,努力不懈地發出噪響。語言是可以被禁止的,圖像是可以被識別並進行管控的,人的行為是可以被規訓的,但聲音呢?聲音是不可言說的,是肉眼不可捕捉的,是可以各自表述的,因此它是難以被歸檔管控的,但又能強而有力地直擊每一具肉身。天文台迥異的樂音與例外的聲響結構,是對聽覺秩序的直接挑釁,像用小刀率先劃出一道破口、鬆解關節,持續且堅定地撐出與體制、服從、麻痺間的距離。
天文台前成員Vivian Wang在訪談裡曾說:「當我們成立天文台時,我們就認為這個樂隊不是一個自我吹捧的工具。它不是我們的財產。我們希望天文台是一個自由的空間,用於不受約束的創造性探索,用於反映和評論在地的問題、生活和任何與人類生存有關的東西。」(註8) 天文台從來就不只是一支「樂隊」,而更接近一個「行動單位」、一種「概念」、一個可能的「空間」。在2022年,他們甚至推出了一場名為《REFUSE》的大型展覽,該展覽的構成以真菌、菌絲體與地下網絡為核心,關注培養品中的菌絲如何為分散的聲音網絡提供動力,插入菌絲體底部的兩根銀針負責發送和接收電流,電流信號被送至一個數位處理器中,該處理器將對天文台所創作的音樂片段進行重組。
REFUSE by The Observatory on Youtube
《REFUSE》不僅意味著天文台樂隊對於「作者」身份的拒絕(真菌才是展覽中真正的創作者),也可理解為重新融合。分解與重構、人類與其他非人類行動者的關係、一種非人類中心主義的視角,在《REFUSE》中不斷被重複提出。從其作品到最新的這場展覽,一貫而終的是天文台對於權威、去中心化的探問與挑戰,不管是體制與個人的關係,還是人類與其他非人類行動者之間的階序,而「持續的重塑」可能是一個解方,對天文台樂隊來說,新的壓迫形式僅能以新的抵抗策略來積極應對,而他們的樂音將是嚮往新世界的人們的行進之曲。
給我一個新的生活
給我一個新的生活
像早晨一樣自由
像夜晚一樣自由
—天文台樂隊,〈廢壞人生〉(Waste Your Life)

TheCube Forum Music Festival—SONIC SHAMAN, The Observatory Performance, 2022.12.08, The Wall Live House, ©TheCube Project Space, photo by Hsuan Lang Lin
參考資料:
- “The Observatory Is Alive: Deciphering The Unleashed Chaos Of Its Current Iteration,” Life in Arpeggio
- “S’pore band The Observatory takes time for reinvention,” Today Online
- https://theobservatory.com.sg/About-2
- 袁志伟:新加坡地下音乐
- https://theobservatory.bandcamp.com/album/demon-state
- Singapore Music –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Local Bands
- 《「依法治國」的迷思:新加坡國家威權法治史》(2021),喬西.拉賈